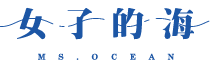【徜徉影海】水與自由(三)關於家園
文/廖芸婕 刊頭照片/悲傷草原劇照
邀我分享電影的編輯問我,在第三篇文章中,是否將為讀者「解決」。他用了相當美的譬喻:「就像是妳帶著聽眾一直在和弦上快速即興,一方面考驗觀眾是不是有功力跟得上妳,另一方面觀眾也期待著聽到音樂被解決,回到主和弦的根音,做一個ENDING。」
───
假若所有的自由,都來自於對遠方未知事物的嚮往,那麼在離鄉背井後,是否將回望自己所來的方向?假若天空中落下的一滴滴雨水,與川河湖海都來自相似的源頭,那麼在奔流不息的永恆中,是否也總回歸同樣孕育潤澤的地方?
藉由「水與自由」,前兩篇文章分別探索了極限與邊界,第三篇或許是重返來時路──家園──的時候。這篇只分享兩部電影:《悲傷草原》與《流浪者之歌》,故事背景都位於臺灣主流視野外的巴爾幹半島。受亞得里亞海、地中海、黑海環繞的巴爾幹半島,充滿山脈與丘陵,孕育了許多極限運動好手。與亞洲之間的一塊內海,則是世界上最小的一塊海洋:馬摩拉海。
這塊受水包圍,昔稱「奶與蜜的土地」,本應是受祝福與眷顧的地方。然而,由於上個世紀領土、主權糾紛不斷,成了兵戎交接的歐洲火藥庫。六年前春天造訪時,我仍見路上留有坦克車的路牌標示;許多家族至今仍受家破人亡所苦,許多民族對離散及顛沛的經歷仍記憶猶新。
此外,這也是許多羅姆人(Roma,舊稱吉普賽人)定居的地方。素來遭受歧視的羅姆人,縱然在東歐許多國家受社會福利政策的保障,然而這樣的賦予,也成了當地主流族群與羅姆人之間的爭端。
《流浪者之歌》便是塞爾維亞導演庫斯杜力卡(註)以羅姆人命運為題的電影。(由於1988年這部電影發行時的名稱為《Time of the Gypsies》,以下忠於原作,稱「吉普賽人」。)其中大量使用以水為題材的畫面,揭示吉普賽流浪命運中的荒唐與深情,當黑色幽默與純粹的童真重疊時,一段關於成長的故事,竟令人心如刀割。成長,究竟是祝福,抑或是詛咒?家園,究竟是港灣,抑或是再也回不去的他鄉?

在一幕如夢的場景裡,男主角與愛人赤身躺在一座小船中,靦腆地嬉樂,在眾人手舉火把點亮的河流中漂行,有如一場婚禮。這樣的浪漫原是男主角的冀望,然而當這樣的冀望終於在數個月後有機會開花結果時,離鄉打拼後又返鄉的他,卻早已成了絕望之途,失去做夢的能力。
「如果沒有夢,吉普賽人還是吉普賽人嗎?或就像一座沒有屋頂的教堂,一口啞了的鐘。」他跳進河水裡救起小貓,想起祖母說過的話。「我愈是絞盡腦汁想知道該怎麼辦,我的腦就愈震盪,而我也離真理愈遠。那時我告訴妳:『我自從逮到自己說謊後,就已經不再相信任何人』,妳告訴我:『若你再也無法相信,那麼上帝會遺棄妳。你會對上帝和對人都不好。』」
踏入現實社會,逃不過謊言世界的爾虞我詐,便將自己也成為一名騙徒,自有一丁點妥協的那一刻起,就踏上了無法回家的路──這樣的暗示,用在刻劃吉普賽社會、或任何少數族群的社會中,都相當適用;然而,即使套用在描述身處類似文化環境中的我們,自幼年長為成人而失去純真的過程裡,相信也有不少人同樣因共鳴而心碎。
《悲傷草原》講述的,同樣是在顛沛流離中成長、在浪跡天涯中遭遇現實的故事。以一次大戰後的希臘為題,導演安哲羅普洛斯再次以大環境下小人物的感情波折,傳達自己對家園的深厚情感。
即使是悲劇,安哲羅普洛斯的畫面依然浪漫得令人屏息:村莊浸水後的家戶行船、草原中的馬匹停駐著凝望隨風飄揚的新娘禮服、大船停靠的海港、雨中與失散的雙胞胎重逢……

與許多描述大時代下的家庭故事相仿,雖每世代的性格各有不同,卻似環環相扣地導向了無可避免的悲劇。《悲傷草原》甚至在希臘內戰的脈絡下,讓好不容易重逢、彌補天倫之樂的家人,走向自相殘殺的命運。
不知為何,許多講述家園的電影都喜愛使用水與火的意象,似乎暗示大自然、大環境的力量足以宰割個體。(寫到這裡,我又想起塔可夫斯基的《鄉愁》。)
老樣子,這篇也不想過度詳細地講述劇情。或甚至該邀請大家拋開任何詮釋,帶著你對於大自然的嚮往,細細地品嘗這些蘊含水、自由、家園的故事。
我無意對任何開放式的題材加以「解決」,又或者,這般的探索將導向愈來愈多的謎團──或許每人看見的是不一樣的世界,不同的故事情節,不同的理解。然而,唯有當作品真正地進駐了每個人的內心,多采多姿的靈魂的能夠與其產生各異其趣的交會,我們對他者的想像,也才有機會更誠實地回到自身的樣貌,放在最純粹、最適得其所的位置。
註:「庫斯杜力卡」沿用臺灣翻譯。然實際上,Kusturica若依塞爾維亞語來唸,或應翻譯成庫斯杜力「擦」或「查」較為忠實。